談起歷史上東西方之間的國際交通線路,“絲綢之路”久負盛名。誠如學界所述,“絲綢之路”一詞最早由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在他的五卷本《中國》里,第一次將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中國與中亞等地區(qū)間以絲綢貿(mào)易為媒介的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主要指西北絲綢之路,又稱“綠洲絲綢之路”)。這一名字后來得到了中外學者的普遍認同,被廣泛地用于指代東西方之間的國際交通線。它不僅僅是經(jīng)濟貿(mào)易之路,更是人員往來之路、文化交融之路、宗教傳播之路、技術(shù)交流之路,在人類文明史上占重要地位。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提出,“絲綢之路”應包括“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以及“南方絲綢之路”。其中,南方絲綢之路開通時間最早,公元前4世紀以前便已存在。但是,長期以來對南方絲綢之路的研究相對薄弱。近來,深研巴蜀古代文明、長江流域古代文明和南方絲綢之路的四川省社科院三星堆文化與青銅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段渝和該院研究員鄒一清的新著《南方絲綢之路史》由巴蜀書社出版,填補了南方絲綢之路通史性著述的空白,亦是當前我國關(guān)于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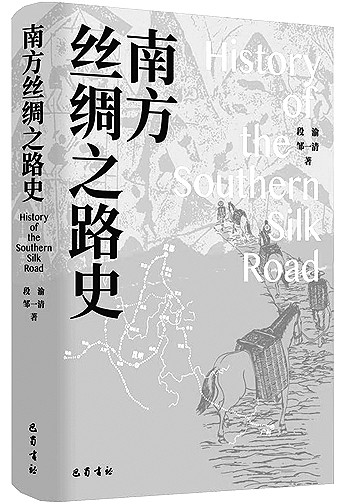
對于“南方絲綢之路”這一概念,以及歷史上南方絲綢之路的形成與各時期指代的主要道路,該著在前言和按先秦、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元明清歷史時期劃分的六章中,進行了概括卻不失精細的介紹。作者指出,歷史上的南方絲綢之路以成都平原為中心,“先秦時期,從四川經(jīng)云南西出中國至緬甸、印度的國際交通線已初步開通”,而“古代四川、云南與南亞、中亞、西亞的文化交流和互動,都是經(jīng)由這條道路進行的”,“由于這條古老的國際交通線位于中國的南方,所以被學術(shù)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這一定義,符合歷史實際,早已為學術(shù)界所接受。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在大夏(今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帶)見到了邛竹杖、蜀布,“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中國古代對印度的稱呼之一)又居大夏東南數(shù)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這段話的意思是,張騫在域外見到了蜀布,行經(jīng)的道路險要,羌人不喜歡,再北一點又是匈奴控制的區(qū)域,因此他發(fā)現(xiàn)了一條通往蜀地、沒有“寇”的良道。這成為漢武帝開拓西南地區(qū)的重要原因之一。關(guān)于“蜀布”,饒宗頤曾在《蜀布與Cīnapatta——論早期中、緬、印交通》一文中論述,“人只知為蜀賈所賣,故稱之為蜀布”。在書中,作者引述印度學者文章論證,成都平原的絲織品進入南亞次大陸,在印度古代文獻中有較多記載,如詩人迦梨陀娑的詩句。該學者還指出,在公元前4世紀至前3世紀早期階段,印度人不太了解中國織物的材質(zhì),分不清“布”和“絲”。
至于中國絲綢在南亞出現(xiàn)的時間,及其與“中國”稱謂的關(guān)系,伯希和、季羨林等都有過研究。季羨林在《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中推測,早在公元前4世紀,“中國絲必已輸入印度”。伯希和認為,在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2世紀間“印度人開始知道有中國,好像是這條道路上得來的消息”。在此基礎上,該著進一步進行了討論,作者在利用最新考古材料對成都平原絲織品出產(chǎn)與行銷范圍進行分析之后,提出三星堆文化時期已形成“錦繡之路”的貿(mào)易交通現(xiàn)象。
該著還通過文獻梳理和考古發(fā)現(xiàn),對存在于中國西南與南亞、東南亞等地區(qū)的“海貝之路”“象牙之路”“茶馬貿(mào)易”進行了勾勒,豐富了南方絲綢之路物資流通貿(mào)易和道路交通范圍的研究內(nèi)容。不僅如此,該著在這些方面的討論,還彰顯了古代文化和文明跨地域交流的特征。以文明互通、互鑒、互融的理念來看待南方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fā)展,正是該書寫作的特色和優(yōu)點。
從古老的“蜀布”“絲綢”等概念在中外典籍中出現(xiàn)開始,南方絲綢之路這條古代國際交通線路就已存在。它以成都平原為起點,向南輻射,主要經(jīng)云南,連系今越南、緬甸、印度等國家,可達東南亞、南亞和中亞、西亞地區(qū);東南經(jīng)廣西等地可連我國東南沿海,連接海上絲綢之路;往北通過金牛、子午、褒斜、儻駱、米倉等“秦蜀古道”入中原,與北方絲綢之路相連。該著對這個交通網(wǎng)絡體系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格局進行了復原,其中又以向西溝通南亞,向南、東南溝通東南亞和我國嶺南、南海地區(qū)的通達狀況為主,精準指出——“縱觀整個南方絲綢之路,在國內(nèi)形成了橫貫我國西南及南方地區(qū)的巨大交通網(wǎng)絡,在國外則與中南半島、南亞次大陸、中亞、西亞連成一個更大的世界性交通網(wǎng)絡”,這便是歷史上的南方絲綢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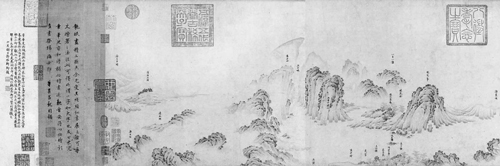
該著對先秦至元、明、清各個歷史時期以成都平原為中心構(gòu)成的主要對外交通線路的開通、修復等經(jīng)營,所依賴的政治形勢、經(jīng)濟條件,所促成的沿線地區(qū)政治、經(jīng)濟格局,以及人群社會、宗教文化等交流局面的敘述,均認識深刻,頗見功力。例如,著作指出,秦漢王朝在巴蜀置郡、移民、發(fā)展經(jīng)濟等舉措,讓巴蜀“從獨立王國形態(tài)和民族性質(zhì)的文化,轉(zhuǎn)化為秦漢統(tǒng)一王朝的地域形態(tài)和中華民族組成部分之一的中華文化亞文化”,也讓秦漢王朝得以“利用巴蜀作為開發(fā)西南夷地區(qū)的基礎,其間尤其加強了對南方絲綢之路起點——成都的建設”。
作者對成都作為南方絲綢之路上的國際都會,以及巴蜀地區(qū)經(jīng)濟、文化、社會之于南方絲綢之路重要性的考察,不僅改觀了以往研究較為重視交通區(qū)位“節(jié)點”考察,缺少經(jīng)濟貿(mào)易、社會文化“具象”復原的局面,也有助于理解歷代王朝對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地區(qū)治理的歷史脈絡。對四川之外的云南、貴州、廣西等地區(qū)政治、經(jīng)濟、貿(mào)易、社會和文化情況,以及南詔、大理于唐五代、兩宋時期在南方絲綢之路交通中發(fā)揮的作用,該著也有較多闡述。通過作者的細致考察與嚴謹論述,讀者能感受南方絲綢之路上“何類不繁,何生不茂”,交流無遠弗屆。
該著還重視對制度進行考察。史籍記載表明,從漢武帝時期開始到隋唐的近700年間,中原王朝或蜀漢當?shù)卣?quán)在溝通和開發(fā)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地區(qū)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四川西南部、云南設置越巂、益州、永昌等郡,在郡以下設縣,對保障南方絲綢之路暢通及當?shù)亟?jīng)濟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書中梳理了秦漢、隋唐等時期中國西南乃至安南等地區(qū)實行中原行政制度、科舉制度的情況,從多維視角展現(xiàn)了南方絲綢之路上制度交流互鑒的影響力。明清時期,中原王朝對西南地區(qū)的統(tǒng)治和治理逐漸加強,著作對此背景下驛站設置、官道開通與完善情況做了研究。官道建設和驛站制度的實施,極大提升了南方絲綢之路的通達性,加深了沿線地區(qū)各民族的往來,故而證明,南方絲綢之路在我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塑造、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化進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南方絲綢之路史》一書,對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地區(qū)的民間交往、人文交流也做了翔實考察。比如,通過青銅器考古資料和文獻里的“枸醬”等流布的記述,讓“蜀商”群體躍然紙上。隋唐時期,活躍于南方絲綢之路上的僧侶,讓中外文化交流呈現(xiàn)出了新的氣象,本土的中醫(yī)藥文化、茶文化西傳,佛教、制糖術(shù)等回傳印度,無疑是南方絲綢之路上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補充。對宋代商人于緬甸地區(qū)貿(mào)易的貢獻,元、明、清時期土官、土司群體在毗鄰東南亞、南亞地區(qū)維護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經(jīng)濟等方面發(fā)揮的作用,該著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描繪。
《南方絲綢之路史》以通史概說為形式,以展示文明交流為主旨,將擁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南方絲綢之路娓娓道來,實證了它在文明交流史上的地位——不同地區(qū)、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人們經(jīng)由這條道路友好往來、交流互鑒,促進了東亞大陸與東南亞、南亞地區(qū)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宗教、藝術(shù)交流。
時至今日,絲綢之路所包含的深厚內(nèi)涵、所承載的多元文化,已經(jīng)遠遠超過“路”的概念。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薪火相傳,絲綢之路成為沿線各國、各地區(qū)人民友好往來的紐帶。事實上,南方絲綢之路也如此。兩千多年來時光向前,但這條道路卻一直延續(xù)不斷。如果說歷史上形成的“草原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都依其途經(jīng)地理環(huán)境的明顯特征而有所指涉,那么這條南方絲綢之路以何可冠?它通過的地理單元更為復雜,高山峽谷似不足指代。兩千多年前,張騫稱其為“從蜀宜徑”,跳出他所處的時局,從文明交流的層面來看,南方絲綢之路或許是一條需要再辟新解的“道路”。《南方絲綢之路史》足以在這方面讓讀者獲得許多新知,做更多思考。
來源:光明網(wǎng)






 掃一掃分享本頁
掃一掃分享本頁



















